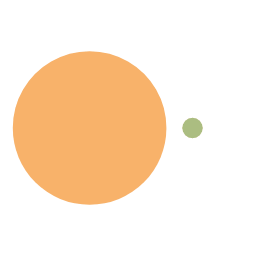商鞅的智囊门客——尸佼
今天,我们来谈谈商鞅团队当中唯一留下姓名的人物:尸佼。
尸佼,“尸体”的“尸”,“佼佼者”的“佼”。
名号一报出来,你可能就觉得奇怪了:怎么会有人拿“尸”当作姓氏呢?
这其实是文字简化带来的困扰,在简化之前,“尸体”的“尸”并不是这么写的,而是写成“屍”,上半部分是“尸佼”的“尸”,下半部分是“死亡”的“死”。在古汉语里,表示**“屍体”的“屍”和尸佼姓氏的“尸”分别是两个字**,简体字把它们合二为一了。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尸佼正是诸子当中的一子,百家当中的一家。但为什么今天很少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呢?这首先要怪司马迁。
《史记》记载诸子百家,篇幅有详有略,略的部分过于简略了,只是一笔带过,说诸子百家当中,楚国有尸子和长卢两位。这就算交代完了,连人家的思想主张都只字未提。
这位尸子就是尸佼。难道司马迁看不起尸佼,或者尸佼只是一个太小的角色,确实不值一提吗?都不是,司马迁的理由是:这些人的作品流传很广,大家都不陌生,就没必要在《史记》里边多费口舌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司马迁经常高估书籍的传播力,但这也算人之常情,谁能想到当下躲都躲不开的流行读物将来会连一本都找不到呢。
后来,《史记集解》搬来汉朝学者刘向的《别录》,解说尸佼的身世和《尸子》这部书的来历,说尸佼不是楚国人,而是魏国人,做了商鞅的门客。商鞅在秦国搞变法,各种事项都是和尸佼一起商量出来的。商鞅被杀之后,尸佼害怕受株连,就逃亡到了蜀地——应该是今天的成都一带——然后著书立说,书有 20 篇,6 万多字。
《别录》的这些记载虽然查无旁证,但《别录》本身很有权威性。
因为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又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大战,所以新建立的汉朝不但满目疮痍,还是一片文化沙漠,找遍全国都找不出几本书来。汉朝政府花了几代人的工夫来搞文化重建的事业,刘向、刘歆父子就是这项事业里的两位主将。
汉成帝时代,刘向主持全国范围的图书校订、整理工作,每整理好一部书,就写一篇整理说明,概述这部书的来龙去脉、内容要点、篇幅字数。就这样日积月累,20 多年间的一篇篇整理说明结集成书,称为《别录》,一共 20 卷。
到刘向去世的时候,图书整理工作也没能完成。刘歆子承父业,还给《别录》瘦了身,编成一部《七略》。《别录》和《七略》可以是说中国最早的目录学专著,可惜都已经失传了。侥幸的是,班固编写《汉书》的时候,专门做了一篇“艺文志”,相当于给当时的图书做了一份档案,材料来源主要就是《七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文献传承的脉络了:先有刘向的《别录》,然后刘歆把《别录》删繁就简,又添了一些新整理的内容,编成《七略》,最后班固把《七略》拿过来,没做太大改动,编成了《汉书·艺文志》。这样一看,《汉书·艺文志》对《尸子》这部书的记载应该只是比《别录》的记载简略一些而已,而事实上,除了简略之外,内容竟然有一处很要紧的差异,说尸佼在商鞅那里并不是普通的门客,而是被商鞅尊为老师的。
刘歆和班固也许看到了什么新材料,但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能被商鞅当成老师,又深度参与了变法谋划的人物,肯定不是等闲之辈,他会有怎样的高明见解呢?这就需要看看《尸子》这部书了。
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在司马迁的时代里还很常见的《尸子》,传到宋朝就已经找不到全本了,很快就彻底失传。明、清两代,学者们从古籍的各种引述当中搜集《尸子》的只言片语,编成《尸子》的辑佚本。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失传已久的《群书治要》从日本传回中国。这部书是唐朝魏征主持编订的一部大型文摘,里边刚好摘录了《尸子》 20 篇当中的 13 篇。有了这些内容,再加上明、清两代学者的辑佚成果,我们终于可以和尸佼先生面对面了。既然尸佼是商鞅私人班底里的重要智囊,甚至还是商鞅的老师,我们很容易觉得他的著述应该和《商君书》是一路的,礼义廉耻通通扯掉,一味追求富国强兵。然而事实上,《尸子》这部书竟然很像儒家作品。
在《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系统里边,《尸子》在一级分类上属于“诸子”,在二级分类上属于“杂家”,这就意味着,尸佼虽然是诸子百家当中的一号,但学术思想有点兼收并蓄的感觉,没法归入任何一家。如果告诉你《吕氏春秋》也属于“诸子”分类下的“杂家”,而且就排在《尸子》之后,你应该就更好理解了。“杂家”是《尸子》的内核,而在这个内核上披着厚厚的儒家外衣,也许当时尸佼隐居蜀地著书立说的时候,有过刻意隐瞒自己和商鞅的关系吧。
《尸子》反反复复谈及“正名”问题,把“正名”当成政治枢纽。书里有几句韵文是这么说的:“正名去伪,事若化成;苟能正名,天成地平。”大意是说,只要做好了“正名”工作,去伪存真,那么政治自然就会变好,全宇宙都能恢复健康。(《尸子·发蒙》)
这里顺便提一句,尸佼还专门解释过“宇宙”这个词的涵义,说“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辑自《世说新语·排调》刘孝标注)这虽然没有文字学上的依据,却能反映出战国时代的高知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
话说回来,被尸佼反复强调的正名,乍看上去很像孔子那套理论,但细看就会发现不同:《尸子》的“正名”,本质上就是刑名学家的循名责实,要统治者根据名与实的相符与否给予相应的赏罚,赏罚的权柄要由统治者垄断,独断专行。统治者要给出一贯的、准确的、便于考核的标准,只要把考核做到位了,一切就都能按部就班。尸佼还拿土地耕作方式的不同标准来举例子,你一定会觉得很熟悉。尸佼说的是,在耕作公田的时候,虽然统治者下达了指令,但种田的人总会消极怠工,反正都是一群人一起劳动,出力多和出力少都差不多。如果取消公田,把土地分给个人承包,生产效率马上就高起来了,因为谁出力,谁不出力,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出力的人没法像以前一样蒙混过关。(《尸子·发蒙》)
尸佼还会用小故事很生动地解释名实关系,说齐国有个人名叫田果,给家里的狗取名叫富,给儿子取名叫“乐”。有一天家里筹办祭祀仪式,狗跑进来捣乱,田果对着狗说:“富,快出去。”祭祀主持人说:“你这话可不太吉利啊。”果然不吉利,没多久儿子死了,田果边哭边喊着儿子的名字:“乐啊!”旁人听了,也不知道这家到底在办喜事还是在办丧事。(辑自《太平御览》 735 卷,905 卷,《艺文类聚》 38 卷)
尸佼推崇能人政治,这点有墨家的味道;推崇“君逸臣劳”的组合,这点有道家的味道。
所谓“君逸臣劳”,简单讲就是国君不做事,臣子忙得团团转。尸佼拿春秋时代郑简公和郑国总理子产这对组合来做这方面的典范,说郑简公对子产这么交待过:“如果饮酒没能尽兴,钟鼓不能长鸣,那么我就该被问责;如果国家得不到治理,朝廷没有秩序,外交活动总是吃亏,那么你就该被问责。你别干涉我吃喝玩乐,我也不干涉你治理国家。”就这样,郑国发展得欣欣向荣,就连孔子都表扬郑简公。(《尸子·治天下》)
当然,这话没法去和孔子对质,但它说明了在战国时代,像尸佼这样出身不高的知识分子对个人命运和天下政治怀有一种热忱的期待,期待靠个人能力得到国君的充分信任和彻底放权,让自己可以在乱世里大展拳脚,开辟一个美丽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商鞅毕竟还是幸运的,尸佼也算借着商鞅的平台做成了轰轰烈烈的事业。至于《尸子》这部书,假如它有生命,并且可以为自己代言的话,我想它会喜欢莎翁的历史剧《亨利四世》里,男一号亨利四世的一句台词:“我深居简出,凡在庄严的场合出现都要显得花团锦簇,宛如一场盛宴,以其罕见铸成其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