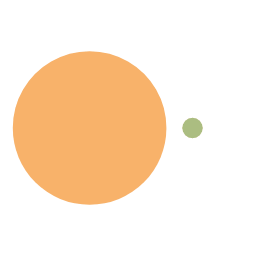《资治通鉴》的纪年逼格
读不懂的第一句
我想,拿起《资治通鉴》的人,读到这一句,一多半的人可能已经打退堂鼓了。
总共 11 个字,除了“起”和“尽”认识,跟在它俩后面的“著雍摄提格”是什么,“玄黓困敦”又是什么,简直高深莫测。
这一讲,咱们就从这打哑谜的 11 个字讲起。
不用怕,著雍摄提格、玄黓困敦,只是你不熟悉的古代的纪年方式:木星纪年里的年份名称。
所以,这句的意思是:
记录周代历史的这第一卷,开始于著雍摄提格这一年,结束于玄黓困敦这一年。
至少早在商朝,古人就发现了木星运行的规律:木星的轨迹和黄道带非常接近,木星运行一周天大约要花 12 年,那么,把木星划过的天区平均分成 12 份,每一份就对应着一年。
只要观察木星现在落在哪个天区的哪个位置,就能基本准确地读出当下的时间,这就是古代中国的木星纪年法。
数字“12”既然有这样的出处,所以就显得格外尊贵,被称为“天之大数”,由此衍生出十二生肖。
古人还把天穹一分为四,称为“四象”。分别是: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
在黄道带上,每一象再分为 7 个区域,四七二十八,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二十八宿。木星 12 年走完一个周天,每一年走过的区域称为一“次”,或者说一个星次,由此衍生出“次序”、“依次”这些常用词。
星次的名称非常古雅,分别是:星纪、玄枵(xiāo)、娵訾(jūzī)、降(xiáng)娄、大梁、实沈(chén)、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这就是中国版的黄道十二宫,明朝人曾经拿这些名称来对译西方的黄道十二宫。
这十二宫,或者说十二星次,可以分为四组。四象的每一象包含三个星次,在这三个星次里边,中间那个对应三个星宿,两边的两个各自对应两个星宿,这就构成了十二星次和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古代中国的占星术就是从这些关系出发来推衍吉凶祸福的。
事实上,木星运行一周天并不是 12 年整,而是 11.86 年。这就意味着,每 12 年就会积累出 50 多天的误差。
到了汉朝以后,天文观测才变得精密起来,开始用坐标来标注星次,于是,那种想像中的星次和星宿一一对应的明确关系就被复杂的现实瓦解掉了。但这还不够,古人又想出了一个简便方案:假想天上有一颗星,和木星差不多,但运行一周天恰好就是 12 年。这颗假想出来的星体,叫作“太岁”。
既然是假想出来的天体,当然可以怎么方便就怎么安排,除了让它运行一周天刚好 12 年之外,还要让它和木星的运行方向相反,这样一来,太岁的十二星次在次序上就可以和十二地支一致了。
地支总是和天干配对的。天干一共 10 个,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一共 12 个,分别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古人用天干、地支搭配计时,12 个地支配 10 个天干会余出两个,这两个再从天干开头的甲、乙开始搭配,配到 60 次之后开始重复,每 60 年叫作一个甲子。
天干、地支的起源非常古老,至少在商朝就已经成型了。
有学者推测说,天干源于以太阳计时,地支源于以月亮计时。另外也有推测说:天干来自某个采用十进制的部族,地支来自某个采用十二进制的部族,后来两个部族融合,天干和地支也就开始搭配使用了。
12 地支刚好能和 12 星次一一对应,但问题是,两者偏偏顺序相反,这会在操作层面上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假想一个太岁,让太岁的十二星次和地支的顺序一致,这真能让人轻松很多。
太岁的十二星次有一套全新的名字,分别是:摄提格、单阏(chányān)、执徐、大荒落、敦牂(zāng)、协调洽、涒(tūn)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
接下来,阴阳观念就该发挥作用了。
阴阳观念是中国人非常核心的思维定式,万事万物皆分阴阳,即便是生病,任何一种病都能分成阴阳两种,或者叫虚症和实症。
比如常见的肾虚就分肾阴虚和肾阳虚;还有感冒,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虽然字面上是寒和热而不是阴和阳,实际上还是阴阳二分法。
太岁和木星当然也会被纳入阴阳系统。木星在天空运行,天属于阳,所以太岁应该在地上运行,地属于阴。进一步推演,木星属阳,太岁属阴,太岁的十二星次因此叫作岁阴。
既然太岁的十二星次配十二地支,称为岁阴,那么,还应该有一套对应的天干,称为岁阳。
10 个岁阳就这样被编排出来了,也有一套奇怪的名字:阏逄(yānpáng)、旃蒙、柔兆、强圉(yǔ)、著(chú)雍、屠维、上章、重(chóng)光、玄黓(yì)、昭阳。
《资治通鉴》就是用这套太岁系统来纪年的,所谓“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如果用我们熟悉的干支系统来表达,就是“起于戊寅年,止于壬子年”;再转换成公历,就是“起于公元前 403 年,止于公元前 369 年”。
岁星纪年与历史观
弄明白木星纪年是怎么会事,那你可能会奇怪,“著雍摄提格”这些词,不光我们今天看来很生僻,一般读古书,常常见到的,也都是“戊戌九年”或者“庆历四年春”这种干支纪年法,或者年号纪年法。
为什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偏要用岁星纪年呢?是为了存心掉书袋,显摆自己有学问吗?
首先,刻意复古,会让人感觉这部书很庄重,很专业,很有格调,尤其是,和王安石变法所掀起的锐意革新的新浪潮格格不入。
其次,《资治通鉴》在纪年称谓上的别出心裁,还有一个很实际的缘故:编年史需要把历史事件准确编年,这需要天文历算方面的专业知识,技术门槛很高。
司马光并没有这个本事,所以他请来当时天文历算方面的大权威刘羲叟负责编年,而这位刘羲叟特别推崇唐朝的《大衍历》,《大衍历》恰恰用到太岁纪年的那些怪词。
无论太岁纪年还是干支纪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客观性。
天文历算在古代中国是一门很高级的学问,关乎政权安危,严禁私人研究。一位官员或贵族,就算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罪过都不如夜观天象来得大。这就让历法有了高度的主观性,和政治立场紧密相关。
《资治通鉴》如果采取常规的编年方式,那么“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就应该写成“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周烈王七年”。
这很好理解,既然写的是周朝的历史,自然该用周朝的官方纪年。事实上,在后面的正文当中,《资治通鉴》确实用的是周朝的官方纪年。
但前边必须要戴一顶太岁纪年的大帽子,这不但有了客观性,避免了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还让全书的编年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统一性。
请天文历算专家协助修史,通常会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怪力乱神太多,让正史看上去很像玄幻小说。
刘羲叟已经算是很有科学精神的专家了,但即便是他,也免不了这一行的职业病,经常搞预测。
比如有一年月亮进入太微宫,他据此推断后宫会有丧事,果然没多久真有一位贵妃过世。又有一年先后发生了日食和超新星爆发,他认为这是辽国皇帝驾崩的征兆,这一回他又说对了,至少元朝人编写的《宋史》是这样记载的。《宋史·儒林二》)
古人研究天文历算,总会和政治挂钩,从自然界的反常现象预测人间万象。司马光可不愿意让《资治通鉴》带上这种调性,所以给助手们定下了严格的甄别标准。
我们今天读《资治通鉴》,会发现它比《史记》《汉书》那些史学名著,尤其比编年史的先驱《左传》更有现代感,玄幻色彩很弱。
《左传》但凡在某一年记载了灾异、占卜、预言,在若干年之后的记载里总能够找到应验。但《资治通鉴》几乎完全避免了这种情况,只保留了极少数的有着特殊警示意义的怪力乱神事件。
北宋是一个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知识分子对古代圣贤的经典著作都敢于发声质疑,但怀疑的限度到底应该设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儒家传统里,一方面“子不语怪力乱神”,基本等于无神论,另一方面“君子以‘神道设教’”。什么意思呢?“神道设教”这个词出自《周易》,就是统治者巧妙运用神秘主义来治理无知的百姓,这是典型的揣着明白装糊涂。
但“神道设教”分寸其实很难拿捏,所以统治者要么在“神道设教”的时候把自己也给套进去了,变成迷信的牺牲品。宋真宗就是典型,不光是封禅泰山,还搞出一堆到汾阴祭祀后土、到河南拜祭祖宗三陵,还把全国都卷入了对“玉皇大帝”的狂热迷信活动中。要么把无神论立场贯彻到底,敢于改天换地,冲破一切束缚,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是典型。
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时候自然会很谨慎地拿捏分寸,既不能像传统史书那样宣扬迷信,也不太好把迷信彻底扫清,搞成“天命不足畏”的调子。
当我们理解了这样的分寸感,就能够理解《资治通鉴》的整体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