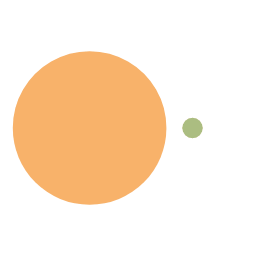礼乐礼乐,守礼之乐
春秋时期经常说礼乐,礼的话可以理解,孔子就是要复兴周礼嘛,那这个乐该怎么看待呢?有一种说法是“乐修内,礼修外”,听音乐真的能让人守礼吗?
“礼”其实包含了“乐”,“乐”是“礼”的一部分,一个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可以说在礼制社会里,“乐”就是“礼”,不存在不是“礼”的“乐”,所以“礼乐”经常合称。至于流行歌曲、靡靡之音,不属于“乐”。
看一个很常见的短语:“礼崩乐坏”,或者“礼坏乐崩”,貌似“礼”是一回事,“乐”是一回事,其实两者都是一回事,“崩”和“坏”也是一回事。说文言的时候,这样表达显得铿锵有力,但如果只要求“辞达而已矣”的话,用白话说成“礼坏了”就完全够了。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你提到的“乐修内,礼修外”的说法一定是相当晚出的,并不合乎礼乐的本义。今天我们理解礼乐,天然会认为“礼”是对外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各种规范,“乐”是对内的,我想听什么音乐完全是我自己的事,关起门,打开音响,自我陶醉就是了——出门在外当然也可以听,只要戴上耳机,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广场舞音乐明显违背了这个规则,让周边的人不得不听,所以引起过很多矛盾。但是,只要我们追本溯源的话,就会发现音乐原本完全没有私人属性,今天人人喊打的广场舞才是音乐的本来面目。那个时候,音乐不是用来听的,而是一种需要人人参与的集体活动。
现代人类学家考察过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可以帮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音乐从来不是一个人坐着聆听的,而是全社会热情参与的。所谓全社会,基本都是几十人的规模。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能发现《诗经》里边就保留着一些原始音乐的遗迹,比如《螽斯》这首诗: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虽然一共有 3 段,用诗歌术语来说叫 3 个诗节,但其实只是字句略有变化,意思一模一样,翻译过来就是:“虫儿嗡嗡嗡,你要使劲生。”诗歌明明是最凝练的语言,为什么可以啰嗦到这种程度呢?
因为它在本质上不是属于私人创作的诗,而是属于集体活动的合唱。
当时既没有钢琴、提琴,也没有笙管笛箫,拍手跺脚就是最好的伴奏了,所以乐句不能太长,不然大家就配合不上,三言和四言因此成为主流的歌词形式。
为了满足合唱效果,一句话还要被抻成好几句。我们可以用白话来模仿一下这种效果:
虫儿嗡嗡嗡,你要使劲生。虫儿哼哼哼,你要多多生。虫儿嗡嗡嗡,你要生生生。
如果还原到这首歌原初的使用场景里边,罗圈话应该还不只这几句,唱完一遍也还会再唱一遍,然后再唱一遍。几百年之后有孔子那样的文化人把歌词整理成文字,删繁就简,很可能还要删掉一些过于粗俗的话,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里边的诗歌样子。
可以想见在很久以前的部落生活里,三亲六戚和左邻右舍们围着一对新婚夫妇载歌载舞,祝福他们多子多孙,这些吉祥话不知道要反复歌唱多少遍。但很有可能的是,这些话不仅仅是吉祥话,或者根本就不是吉祥话,唱歌的人们真诚相信这样一场歌舞仪式可以带来多子多孙的结果。在普通人看来,他们是在唱歌跳舞,而在人类学家看来,他们是在搞巫术,这叫交感巫术 (Sympathetic Magic)。
如果我们读英文原著的话,会发现“交感”这个词其实就是常用词 sympathetic,“有同情心的”,意味着情感和情绪的共通。原始人比现代人更有同情心,这倒不是说他们更善良,而是说他们比我们更加相信万物相通。
巫术就建立在这种广泛的同情心上,所以才会被称为交感巫术。
英国学者弗雷泽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 写过一部人类学名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1890),这部书把巫术原理分为两类,一是相似律 (the Law of Similarity),二是接触律 (the Law of Contact or Contagion)。
我们对相似律其实非常熟悉,它的心理机制就是:相似的东西会产生相似的东西 (like produces like)。比如为什么吃核桃能补脑,因为核桃仁长得很像大脑,简言之,吃什么补什么,吃哪儿补哪儿。接触律的意思是:两个物体只要接触过一次,那么在接触之后,无论隔了多久的时间和多长的距离,还会彼此发生影响——是不是很像爱情?
我们还可以把弗雷泽的理论简化一下,因为无论是相似律还是接触律,本质上都是因果律,只不过用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这些原始人把因果关系搞错了而已。
但无论对错,人家至少知道为了达成某个结果,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种瓜得苹果,种豆得猪肉,谁都别想不劳而获。怎么努力呢?几乎任何一种努力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部落成员的全体协作,这才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日常生活状态。那么不难想见,对全员协作的需求越强,对协同性的需求也就越强。
今天我们依然看得到依靠音乐促进协同性的例子,比如教堂里边,几百名信徒一起念经,他们会用一种很特殊的,介于唱歌和朗诵之间的腔调,让所有人的声音保持一致。在山城重庆,搬运工被称为“棒棒”,靠一根扁担挑着重物上坡下坎。如果搬的是冰箱这种大件,就需要两名“棒棒”协作,一前一后健步如飞,嘴里发出一种介于唱歌和喊号子之间的声音,非如此则不能既稳又快。
人类是天生的猎人,而不是天生的“棒棒”,所以在部落生活里,最核心的协作活动当然就是打猎。怎么才能让狡猾的猎物现身呢?绝大多数的原始部落都会做一件事:唱歌跳舞。在这种歌舞活动当中,有人扮演猎物,有人扮演猎人,大家越唱越跳就越亢奋,而在社会功能的意义上,不但围猎技术因此得到了演练,集体主义精神也因此得到了强化,这两点正是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生存优势。
这样的音乐,在《诗经》里边也能看到遗存,比如《简兮》,描写一种叫作万舞的歌舞场面,处处都和今天的常规歌舞反着来:表演在中午进行,而不是晚上,一群强壮的男性歌舞表演者,而不是婀娜的女性表演者,“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像老虎一样威猛,在领主的庭院里上演着原始版的《速度与激情》。
集体歌舞活动带给人的亢奋感可以让人产生一种神秘体验,感觉个体融入了集体,进而连同这个集体融入了一个更广大,更深邃,更有力量的神秘之物,因此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或者感受到神的存在。
这样的观点最早是由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涂尔干系统性地论述出来的,详情见于他的经典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部书深刻影响了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 布朗 (Alfred R. Radcliffe-Brown, 1881~1955)——1906 年,年仅 25 岁的拉德克利夫-布朗登上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安达曼群岛,开始了两年左右的田野调查,调查结果写成《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 1922),成为人类学的一部经典。我们可以从这部书里看到原始音乐活动的各种写真,有一幕是这样的:一名长者站在一个控制节拍的响板旁边,男人们围成一圈,手拿一种特定的树枝,站在响板旁边的男人一边唱歌,一边用脚踏着响板打起节拍,女人们坐在稍远的地方,男人“一唱”,她们就“一和”,并且用手拍打大腿来打拍子。然后还有一系列的复杂动作,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角色、位置和次序都不能乱。这很可以理解,因为音乐的意义既然如此重大,各种要求和禁忌也就相应地多了起来,甚至会到谨小慎微、繁文缛节的程度。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每个社群成员的各安其位就演变成了“礼”的规范,至于音乐,按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人们很可能仍然保有着“音乐特别重要”的记忆,于是为音乐添加了意识形态的浓墨重彩,甚至认为只要把音乐工作搞好了,治国平天下就可以水到渠成。